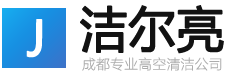巴金和冰心有著70年的深厚友誼,在精神上彼此扶持一直延續(xù)到耄耋之年。從《收獲》雜志近期刊發(fā)的98封兩人來(lái)往書信便可略見他們的情誼。
“得來(lái)信和《文叢》,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斷在努力,尤為興奮。蕭乾的文章,越寫越好了,應(yīng)該傳令嘉獎(jiǎng)。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還是多一點(diǎn)……”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從巴黎寫給巴金的信,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冰心寫給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畫像旁題寫贈(zèng)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dāng)以同懷視之。”同年5月,巴金給冰心的題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盞明燈,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樂觀。燈亮著,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燈亮著,我不會(huì)感到孤獨(dú)。”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溫暖
關(guān)于巴金和冰心之間的友誼的細(xì)節(jié),已有無(wú)數(shù)學(xué)者、作家或是親歷者撰文詳述。
故事的開始,似在1933年。
那時(shí),巴金正在北平小住,與鄭振鐸、章靳以等一起創(chuàng)辦《文學(xué)季刊》。為了給刊物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訪了冰心。
冰心后來(lái)回憶:“那時(shí)我們都很年輕,我又比他們大幾歲,便把他們當(dāng)做小弟弟看待,談起話來(lái)都很隨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談,熱情而活潑;巴金比較沉默,靦腆而略帶憂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時(shí),她已讀過這位“小弟弟”的一些早期作品。她記得,他常愛背誦一位前輩的名言:“當(dāng)我沉默的時(shí)候,我覺得充實(shí)……”他還說過:“我似乎生來(lái)就帶來(lái)了憂郁性,我的憂郁性幾乎毀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沒有一刻停止過。”
“我記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潰的、陳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幾年,他的充實(shí)的心里有著太多的留戀與憤怒。他要甩掉這十幾年可怕的夢(mèng)魘。他離開了這個(gè)封建家庭,同時(shí)痛苦地拿起筆來(lái),寫出他對(duì)封建制度的強(qiáng)烈控訴。他心里有一團(tuán)憤怒的火,不寫不行,他不是為了要做作家才寫作的。”——盡管第一次見面,但巴金與冰心卻如相知許久的故人。
巴金初見冰心時(shí)的沉默,或許還有另一層原因——終見欽慕已久的“長(zhǎng)輩”,難免靦腆。
其實(shí),他們的友情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筆。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園子里,伴著滿園蟬聲讀冰心的詩(shī)《繁星》,邊讀邊學(xué)寫“小詩(shī)”。
雖然只寫了十幾二十首,但巴金說,那些“小詩(shī)”一直鮮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覺得有人吟著詩(shī)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覺地吟著詩(shī)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詩(shī)在前的,也許就是冰心。
巴金后來(lái)曾有過這樣的回憶:“當(dāng)時(shí)年輕的讀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們喜歡冰心,跟著她愛星星,愛大海,我這個(gè)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溫暖。”
1923年5月,巴金離家赴上海。經(jīng)過瀘縣時(shí),他特地上岸買了一本由商務(wù)印書館初版的《繁星》帶在身旁。
文字讓原本陌生的兩個(gè)人靈犀相通。
他仍是個(gè)調(diào)皮的孩子
有這樣的默契作為基礎(chǔ),兩人初識(shí)的一見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從昆明到重慶,巴金恰好也在這時(shí)來(lái)到重慶。冰心當(dāng)時(shí)吐血,住在歌樂山養(yǎng)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經(jīng)濟(jì)拮據(jù),連年夜飯都成了問題,巴金跟冰心談起她的著作應(yīng)在內(nèi)地重印出版。冰心便將此事全權(quán)交給這位“小弟弟”。
巴金在經(jīng)濟(jì)上的鼎力相助,不僅讓冰心感激,冰心的丈夫吳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個(gè)真誠(chéng)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蕭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舉家內(nèi)遷云南昆明時(shí),巴金曾帶未婚妻蕭珊到冰心家拜訪。
此后,蕭珊任《上海文學(xué)》和《收獲》雜志編輯,巴金常“慫恿”妻子向冰心約稿。冰心喜歡蕭珊,對(duì)她的約稿自然不會(huì)敷衍馬虎。在冰心看來(lái),“那些千把字的雞零狗碎的應(yīng)急文章”是不會(huì)給蕭珊的,她總想“聚精會(huì)神,寫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點(diǎn)的”文章。
慢工出細(xì)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蕭珊難保不連續(xù)寫信催稿。她的信“又熱情,又撒嬌”,有時(shí)甚至調(diào)皮地寫:“你再不來(lái)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給蕭珊的回信中寫道:“你的信來(lái)了,又是‘自殺’,(在這一點(diǎn)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嚇壞了,我連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寫好一并寄去,不料,越著急越不行,就像小學(xué)生寫作文一樣,理不出一個(gè)頭緒來(lái)……納蘭詞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轉(zhuǎn)薄,而今真?zhèn)€不多情’,可為我詠!這兩天又開始努力,遲早寄上,請(qǐng)別著急。少不得請(qǐng)代問巴金好,雖然他仍是個(gè)調(diào)皮的孩子!”
我無(wú)時(shí)不在惦記你
生活注定不會(huì)一直風(fēng)平浪靜。
巴金與冰心兩個(gè)人,或者說兩家人的親密交往,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不得不中止。“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音信隔絕,直到“四人幫”被粉碎。
十幾年光陰,并沒有隔斷兩個(gè)人的友誼。他們始終在心底互念老友,不知對(duì)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筆,給冰心寫了十多年來(lái)的第一封信。他寫道:“算起來(lái)11年了!這中間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幫’的嚴(yán)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寫信,也不愿給別人、也給自己帶來(lái)麻煩……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們的垮臺(tái),我果然看到了……”
正是這封信,帶來(lái)了久違的問候,也讓巴金和冰心開始了北京、上海兩地之間的鴻雁傳書。信中,他們慶幸“重逢”,也談“十年浩劫”。當(dāng)聽聞“又調(diào)皮”“又撒嬌”的蕭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致病而死,冰心更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愛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受邀參加中國(guó)作家代表團(tuán)訪問日本。巴金當(dāng)年76歲,冰心比他還要年長(zhǎng)4歲。訪問期間,兩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地開懷暢談至午夜。
日本一別,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兩位老人年事漸高都經(jīng)不住長(zhǎng)途旅行,他們只有少數(shù)的幾次會(huì)面,1985年后不復(fù)相見,完全靠書信溝通心靈。
巴金即使為病痛所苦,執(zhí)筆困難,手發(fā)抖,但隔些日子也還要勉力而為,給冰心寫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們,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無(wú)法寫信吐露我滿腹的感情。”而冰心則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個(gè)深藍(lán)色的鐵盒里。
即便從未中斷過書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總盼著能有機(jī)會(huì)再見巴金。巴金研究專家丹晨,就曾在回憶巴金和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見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說:“你怎樣?能到北京來(lái)嗎?我們仿佛永遠(yuǎn)也不能見面!”“我無(wú)時(shí)不在惦記你。血壓還低否?手還抖否?”“今年如能來(lái)京一行,相對(duì)談話比寫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們住近一點(diǎn)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們兩人弄到一處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談,不只是牢騷,談些可笑、可悲、可嘆的事,都可以打發(fā)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傷過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進(jìn)醫(yī)院治療。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關(guān)切而焦慮地說:“你近體怎樣?何時(shí)出院?千萬(wàn)不要多見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邊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說:“知你不喝酒,但喜歡茶和咖啡,在這點(diǎn)上又與我相同,什么時(shí)候我們能做(疑‘坐’之誤)到一起喝喝咖啡,談一談,多好!可惜我們都行動(dòng)不便了。”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藥物
和冰心一樣,在不能相見的歲月,巴金也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關(guān)心著自己的大姐。
巴金在1989年寫給冰心的一封信中曾這樣說:“我們不能見面,有話也無(wú)法暢談,幸而我們能做夢(mèng)……我還想,能做夢(mèng)就能寫書。要是您我各寫一本小書,那有多好!”
曾擔(dān)任《文藝報(bào)》主編,并和巴金、冰心有過長(zhǎng)期交往的作家吳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記述過這樣的往事:1985年,冰心的愛人吳文藻去世。冰心對(duì)吳泰昌說:“我暫不給巴金寫信,你將一些情況告訴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過了不久,冰心之女吳青寫信給巴金,巴金在給吳青的回信中說:“聽泰昌說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難過。想寫封信給你,但手抖得厲害,而且這個(gè)時(shí)候講什么話好呢?我只能說:‘務(wù)望節(jié)哀!好好地照顧你母親!’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開的。請(qǐng)她多多保重……”
但讓吳泰昌更為感懷的,還是后面的細(xì)節(jié):1986年5月18日,冰心應(yīng)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請(qǐng)去花房賞花,鄧穎超得知消息后,趕去看望冰心。關(guān)于兩位老人在月季花叢中相會(huì)的情景,吳泰昌寫了一篇散記發(fā)表在《文藝報(bào)》上。
文章見報(bào)后,冰心又叫吳泰昌去,把當(dāng)時(shí)的細(xì)節(jié)詳述給他聽,叫他告訴巴金。吳泰昌說:“巴老看《文藝報(bào)》的,他肯定會(huì)知道。”但冰心說:“你沒有參加這個(gè)活動(dòng),你寫的內(nèi)容是聽我說的,還有一些具體的細(xì)節(jié),再給你講,你告訴巴金,也讓他高興,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擔(dān)心我情緒不好。”
點(diǎn)滴細(xì)節(jié),可見兩位老人幾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確也給晚年的巴金帶來(lái)許多溫暖。
那時(shí),巴金幾次向冰心訴說,有許多干擾,總有人纏著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復(fù)信表示同感。覺得這是“名人之累”,無(wú)可奈何。巴金談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國(guó)家、民族的前途,總是放心不下”。冰心則囑他“不要那樣憂郁,那樣痛苦”。
難怪當(dāng)年冰心為巴金捎來(lái)紅參時(shí),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養(yǎng)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藥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氣。”冰心則在回信中說:“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你有著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與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兩人吃力地寫下對(duì)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寫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復(fù):“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他們留下的,是兩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本文部分細(xì)節(jié)參考冰心、巴金通信和部分著述,同時(shí)參考丹晨、吳泰昌、李朝全等所寫所編回憶巴金、冰心的文章及書籍)
(姍 姍摘自《小康》2012年第19期)
熱門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