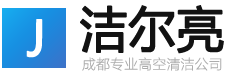1984年3月,加蓬埃丁布埃州州政府,離任的議長程志平和他剛被任命為“總統民事辦公廳主任”的兒子讓·平。
1994年秋,“葉豐YF—HEV”概念型混合動力汽車誕生,但此時的葉文貴已耗盡千萬資產。
編者按:有人說,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不管你怎么努力,也永遠趕不上“官二代”和“富二代”,一些年輕人甚至以此為理由不思進取。還有的年輕人抱怨說,如今一畢業就面臨“就業難”、“高房價”、“裸婚”等現實難題,覺得當代的青年身上背負了太重的負擔。其實,哪一代的青年不是負重前進、承擔著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我們通過下面的故事,給大家講述上一代青年人的奮斗歷程。
1933年,二戰的硝煙即將蔓延,非洲加蓬的港口來了一位年輕的中國人。他是一位販賣瓷器的小貨郎,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流浪者。在他過世20年后,這個非洲國家的議員、平民,提起他都親切地稱為“父親”或“平”。
1985年冬天,20歲的鄉村裁縫周成建生意失敗,回到了一個叫石坑嶺的小山村。20萬元的債務對于一個山里人家來說,是個天文數字。但父親說出的第一句話不是責備,“就把家里的3間老屋賣了吧,先來還債。”
記錄這些故事的是一部歷時8年拍攝完成的紀錄片《我的中國夢·中國溫州人的故事》。這部不久前播出的紀錄片,也是中國第一部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永久收藏的人文類紀錄片。
“我們的兩萬多小時素材,100多萬公里的行程,不僅僅是為了展示18個傳奇故事,更是從一個角度敘述百年來中國人追夢的歷程。現在,可能很多年輕人覺得生活很被動、慌張,甚至坐立不安,對社會和自己缺乏信心,而這18個普普通通溫州人的人生,或許會讓我們感動、震撼、激情重燃,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這部紀錄片的導演葉卉說。
加蓬人民愛戴的中國人
1929年秋,程志平走出溫州臨江鎮的農家院,那一年,他才19歲。自幼父母雙亡的他,是姑媽一手拉扯大的。這一天,姑媽為他安排好了行程,送他前往法國。
1929年,程志平身后的祖國肅殺凄涼。當年9月的《申報》記載,持續79天的旱災加上蟲災,使得米價飛騰,貧民自殺,受饑荒的老百姓達40萬之多,“災情之重,為60年所未見”。不少稍微有點積蓄的人家,都想方設法送子女到海外“碰碰運氣”。
程志平乘坐的郵輪從上海啟程南下,經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穿過紅海、地中海,他就坐在擁擠的底艙。在一二次大戰期間,數以萬計的中國青年,沿著這條線路遠涉重洋,抵達法國馬賽港。
葉卉在巴黎找到了仍健在的第一代中國移民厲言先生,老先生已經90多歲高齡。他回憶,那時眾多華僑到法國后最初的謀生方法,是從老華僑那里批發來小商品,提一個裝著打火機、領帶、燈泡、小瓶香水的手提箱子,沿街推銷。當時語言也不通,華人們最先學會說的就是“拉烏拉,拉烏拉嘞”(賣東西的意思),還有“先生、太太,不貴,不貴”。
“有時法國人發火了,一腳把你踢出去,皮箱在樓梯上面‘咣朗咣朗’滾到下面,里面的花瓶都打壞了,一個星期賺的錢都打水漂了。”第二代華僑、法國華僑華人會名譽主席林加者說。
程志平在工廠打工,沒有掙到錢。臨行前,姑媽給他的最后囑咐是:“不管掙沒掙到錢,3年就回來!”因為家里已經為他訂下了一門親事。但他到了馬賽港,最終買的船票卻不是回中國的。
1933年4月,程志平和他在法國認識的同鄉陳松青,成為踏進當時法屬殖民地——非洲加蓬的第一批中國人。作出這個決定時,他正和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同齡。不難想象,從異鄉法國再去“黑非洲”,需要這個年輕人多大的勇氣。
在說法語和甚至完全不懂的當地土語的環境下,他們穿著僅有的西裝,打著領帶,肩上挑著裝瓷器、小五金的擔子,從街頭叫賣到山村。正當帶來的貨物漸漸賣完時,讓蒂爾港唯一一家面包房的老板去世了。程志平決定接下這家面包房,在加蓬定居。
后來,他用積蓄轉做捕魚業、木材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甚至成為北非盟軍的副食供應商。但是,戰爭也阻斷了回家路。
在程志平逝世18年之后,葉卉和攝制組一行6人乘飛機降落在讓蒂爾港。70年前他待過的老面包房還在,一日清晨,葉卉沿著湖邊散步,甚至見到了二戰時期程志平給北非盟軍運輸副食品的那條老漁船。
令葉卉印象極深的是,在攝像機所拍之處,從參議長到部落民眾,從原住民到法國、希臘僑民,大家依然親切地稱他為“父親”或“平”。57年前他們帶到非洲的織網和腌制鮮魚等技術,如今仍是當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非洲爆發了使很多人破產的木材貿易危機,長時間停在讓蒂爾港的木筏都爛了。歐洲公司紛紛辭退工人,程志平則叫來所有工人,讓他們自己作出選擇:是留下來一起等待危機過去,還是離開。
“他們沒有工資,因為我父親也已經沒錢了,沒有任何業務,但是大家一起種點莊稼、捕點魚,還能有口飯吃。這種情況前后持續了一年。”程志平的兒子讓·平說。但當危機過去,歐洲人辦的企業因為辭退了員工,恢復很慢,而程志平領著一起患難的工人重整旗鼓,迅速發展為當地最大的木材企業家。
在當地的翁布埃原始森林伐木場,伐木的噪音常常會驚擾猛獸。有一次,程志平和工人們遭到了一頭發怒大象的攻擊。在四處逃散的人群中,大象卷起了其中一個人,把他扔起來摔了個粉碎。程志平跑的時候摔了個跟頭,把鼻梁骨摔裂了。
但是,這個中國人在猛摔跟頭中,慢慢學會了非洲的一切,包括土語和怎樣去對付大象。“我父親告訴我,被大象追的時候,你不能跑直線,需要跑‘之’字形。因為大象體積太大,拐起彎來比較困難。他說,這個分寸很難把握,拐早拐晚都有危險。”讓·平回憶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整個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云涌。1960年,加蓬宣布獨立。一直保持沉默的地區首富程志平,出人意料地活躍起來了。
加蓬南部的埃丁布埃州副議長格拉爾德說:“他出資興建了醫療診所和學校,還買來了輪船,解決了湖區的交通問題。這在當地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1972年,埃丁布埃州人民在選舉州議會議長時,把選票投給了這位中國移民——程志平。
他的兒子2008年當選為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每一次完成有生命危險的外交斡旋任務,讓·平都會來到父親墓前,靜靜地待上一會兒。
“加蓬有很多法國朋友勸父親加入法國國籍,他都拒絕了。父親一直說:我是個中國人。”讓·平說。
今天,程志平的后代、親友有100多人,在非洲加蓬經商謀生。
小裁縫的大智慧
1979年,在浙江南部的一個偏遠山村,14歲的周成建如愿當上了鄉村小裁縫。老板管吃住,工資是番薯干和稻米。
上世紀80年代,離周成建家不遠的溫州永嘉縣橋頭鎮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聞名的紐扣集散地。一個月三四百元的獲利,相當于當時一個工人的全年收入。16歲的周成建很快放下了裁縫的活計,和幾個堂兄弟一起下山賣起了紐扣。
那段日子里,讓周成建回憶最久的,是既疲憊又緊張、等待第二天清晨火車的一個個深夜。“我們都住在上海提籃橋的地下室,那是上下鋪的大通鋪,因為怕丟貨,就用鐵鏈鎖把一袋子紐扣鎖在自己身上,甚至把紐扣枕在腦袋下,度過一夜。”
賣了4年紐扣后,覺得賣衣服更掙錢的周成建“稀里糊涂”地跟一個商場老板簽了一單服裝合同。
這是年輕人初次嘗到當“小老板”的滋味。他一個人跑到溫州買了布料,雇工人用扁擔把布料從20公里之外挑到自家村里。只要懂做裁縫的親友鄰居,全都被請到了周家幫工,到夜里都燈火通明。“我記得那1個多月有100多號人在干活兒,很忙的。”
簽下這紙合同的時候,他手頭只有賣紐扣攢下的幾千元,而成本要二十來萬元。為了干成這筆買賣,他鼓起勇氣跑到當地的信用社,貸了15萬元。
但1個月之后,周成建就不得不為這張稀里糊涂簽下的合同“埋單”。
“衣服一運到,人家打開包一看,說你這個衣服沒有尺寸、也沒有規格,最后他說你這個貨不行,不符合合同的要求,拿不到一分錢!”
那一年,周成建20歲。20萬元的債務對當時的他來說,是一個“滅頂之災”。
父親鼓勵了他,把家里僅有的幾間老屋做了個分割。周成建賣了自己的那份,把從隔壁鄰居家借的錢先還上了。“留下來的就只有銀行的債,當時銀行來向我***的時候,我跟他說,我肯定會還掉,請你不用擔心,但是必須要給我一點時間。”
在現在很多年輕人讀大三的年齡,周成建帶著還債剩下的9000元,來到溫州尋找機會。他想的是,如果在家里種田,“估計兩輩子也還不了債,還是去闖蕩吧”。
在花光了最初的那點盤纏之后,周成建還是干回老本行,雇了幾個工人做服裝加工。在這個重新期待曙光的人面前,又一場新的磨難造訪了。
當時的專業批發市場是白天收到訂單、第二天就要交貨,裁剪、排料都要靠他一個人熬夜挑燈來干。在一個疲勞過度的晚上,周成建把衣服裁錯了。轉眼之間,十幾萬元賠款擺在了周成建面前。
無奈之下,他只得挖空心思,尋找補救。“我去買了一些面料過來,原來是西裝袖口,就把它接成夾克的袖口,用配色配起來……”
剛剛改革開放的當時,中國的服裝式樣普遍很單一。周成建把普通的西服這樣一折騰,居然成了市場上的時髦貨。這個偶然的創意讓周成建絕處逢生,他突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自信。
1994年,周成建以50萬元起家,在溫州創辦了一家當時還很冷門的休閑服飾公司,并取了個標新立異的名字:“美特斯·邦威”。
他不是失敗者
在溫州市蒼南縣一個叫金鄉的小鎮,有一位清瘦的中年男人在此隱居了10多年,平日里養著一池子錦鯉,偶爾會到鎮上買買魚食。他已被很多人遺忘,但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葉文貴”曾經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
1978年改革開放后,不足兩萬人的金鄉鎮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鋁制徽章制品集散地。從黑龍江插隊回來的青年葉文貴卻沒有辦鋁制品廠,而是獨辟蹊徑,約了17位親友,每人投資400元辦起了鋁板加工廠,為徽章企業提供原材料。
這家不起眼的小工廠4個月就收回了全部投資,賺的錢遠遠超過了生產徽章的同鄉們。而在旁人的驚羨目光中,葉文貴的PVC薄膜廠建成投產,每噸邊角廢料1000元收進來,加工后2600元賣出去,產品供不應求。
“最緊張的時候,當時一天能掙兩萬多元,做起來像印鈔票一樣……”葉文貴現在站在曾屬于他的紅磚廠房外,淡淡地說。
幾年間,這個青年先后辦了5家工廠,“賺不完的錢,辦不完的廠”是他給那個年代留下的創業名言。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他的廠里轉了3圈后,留下一句這樣的評語:“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
1984年4月8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很特別的消息,個體戶葉文貴就任蒼南縣金鄉區副區長。“個體戶當官?!”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個爆炸性的新聞。而短短3個月后,說自己“不會做官”的葉文貴就掛冠而去。這一年,葉文貴才34歲。
1987年3月10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分行批準,葉文貴的金鄉包裝材料廠開始發行股票,成為中國最早發行股票的私人企業之一。德國《明鏡周刊》派出記者史德安專程到金鄉采訪他。
同年,全國評選出了100名優秀農民企業家,但是,到北京領獎的只有99位。
唯一沒去領獎的當選者葉文貴,正在開始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瘋狂行動——研發中國第一輛電動轎車。
“當時就是想搞個車子玩玩。”葉文貴一邊整理著泛黃的造車圖紙,一邊回憶說,“當時全中國一共有16家轎車廠,自己一個轎車牌子都沒有。所以我覺得,試試看,自己造一個中國人的牌子。還有一個理由:汽油車有污染,電動車沒有污染。”
1988年初夏,溫州最著名的企業家葉文貴“消失”了。他在當年溫州最好的飯店包了一個套房,開始招兵買馬。來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業的各路專家來到溫州,“天天在那兒畫圖”。那是一場與全世界電動汽車研究者同步開始的競賽。
1989年2月的一個傍晚,一輛像玩具鐵皮車的小汽車悄悄從溫州市區開了出來,沒有人注意到它的異樣。車里面坐的是葉文貴和他的3個同事,這是他們造出的第一輛電動轎車“葉豐零號車”。從研發到上路,只用了短短的6個月。
“當時我們一路開上山,我看到下面萬家燈火,往遠處一直看到甌江邊,全看到了!我覺得自己造出一個‘破車子’,能坐4個人,高興壞了……”葉文貴說。
而在同時,世界各大汽車廠商也進行著電動汽車的研發。電池壽命短、車開不遠,漸漸成為各國研究者的共識,遠在中國南方一隅的葉文貴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1989年2月,他專程前往美國考察電動車技術,開始研究動力革新。然后,他在溫州市龍灣經濟開發區的25畝土地上,邀請了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國內33所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前來共同研發中國第一輛混合動力汽車。他的財富就像流水一樣,投到了無底洞般的研發中。
1990年10月,葉文貴成功推出“葉豐—Ⅱ”號車。這是一輛真正意義上的混合動力車,它擁有容量強大的蓄電池組,一次充電可行駛200多公里。同時,裝上了葉文貴自行研制的專用雙缸水冷汽油發動機。在當時,“葉豐—Ⅱ”的技術已占世界同行業領先水平。
在此4年后,德國大眾公司混合動力汽車研發成功。又過3年的1997年,日本豐田普銳斯混合動力汽車研發成功。
1990年10月,一張金字證書從北京寄來,“葉豐—Ⅰ”電動車被國家四部委評選為“國家級新產品”。次年,在深圳的中國電動汽車研討會上,葉文貴和他的汽車一鳴驚人,和別人“裝個電動機,放幾個電瓶”的樣車不可同日而語。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嚴峻的現實擺在了葉文貴的面前:他沒錢了。幾年來,葉文貴投入電動汽車研究的資金已超過2000萬元。
溫州蒼南縣金鄉鎮原黨委書記金欽治回憶:“他當時想得很樂觀,覺得如果拿到國家專利,國家扶持,他能夠上去的。結果資金拿不下來。”
事實上,葉文貴并非沒有機會獲得投資。1991年,溫州市政府和深圳某部門曾進行過一次談判。當時,深圳方面提出把電動車事業變成溫州和深圳共同開發的項目,但溫州方面不同意,說“技術不能轉讓給深圳”。
無奈之下,葉文貴開始出賣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產業。從工廠、房產到果園,在金鄉鎮私營經濟最興旺的時候,他一個又一個地賣掉了自己的產業……
1993年8月,“葉豐—Ⅲ”號車面世。同年,葉文貴收到了來自“北京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申辦委員會”的信函,同意葉豐牌電動車作為未來奧運場館的使用車。他依然抱有一線希望。
同年夏天,一個金發碧眼的美國人萬里迢迢來到了金鄉,他的名字叫羅耶·凱勒(Roy Kaylor),是一位來自美國加州的電動汽車專家,想合作生產或加工。這是葉文貴獲得投資的最后機會。
但雙方的談判卻在成品車掛什么牌子的問題上陷入了僵局。
“我說我要掛我的‘葉豐牌’,他說不行。他說,掛你的‘葉豐牌’進不了美國、歐洲市場,非得用他們美國的牌子。我想,我這樣不是白干了嗎?我替美國人打工了。”葉文貴說。
他放棄了。一周后,美國投資者離開了。
1994年秋天,“葉豐YF—HEV”車型試車。這輛有著漂亮流線型車身的概念車,一上路就吸引了無數人好奇的目光。而當時的葉文貴已是山窮水盡。
1995年5月1日,葉文貴送走了幫他畫完最后一張圖紙的最后一位工程師。然后,他拿自己用了多年的大哥大手機換了一頭毛驢,從此閉門謝客,徹底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10多年過去了,當攝制組造訪時,生滿雜草的老車庫里,那輛在今天看來依然“外型前衛”的第四代紅色樣車,還能開動。在它身上,曾寄托了葉文貴半生的夢想,耗盡了他的千萬資產。
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傳奇企業家說:“對于做車來講,我認為自己已經成功了。別人從做買賣的角度,說我錢投進去就得有投資回報,但這是不好比較的。”
葉文貴已年近花甲。如今,比他晚10年起步的同學、徒弟都已坐擁幾千萬元,有的甚至是億萬身家。但他的夫人說,他的一生相當于別人活了十輩子,非常精彩。
不久前,在家過了10年閑逸生活的葉文貴,接到國內多家汽車工業集團的邀請,希望共享他的獨家專利,重新開發。這個難得的機會,也許能幫他續寫未竟的汽車夢。
每個人都有一個中國夢
葉卉的紀錄片里,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曾遇到抉擇和失望。葉卉在手記中寫道:“他們選擇了繼續前行。他們是一群夢想騎士,無畏是他們活著的姿態。”
白巖松曾在耶魯大學作過一次廣為傳播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他談道:“在過去的30年里頭,你們是否注意到了,與一個又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緊密相關的中國夢。”
葉卉的紀錄片記錄了這些人的中國夢。今天的他們或他們的后代是:美國華人從政的拓荒者、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法國最重要的華裔財富族群、美國國際消費品安全協會主席、臺灣《商業周刊》發行人、世界級工業企業的掌門人、中國知名私立大學的創辦人、中國鞋王及休閑服飾之王……
“對葉文貴,我們有一份額外的敬重。我始終覺得,假如我們的社會愿意包容這樣一種夢想,更多的年輕人也許就不會患得患失、瞻前顧后,而能勇往直前。無論是程志平、葉文貴還是周成建,抑或我們每個人,生命的價值就是活出自己的那份色彩。”葉卉說。(莊慶鴻)
熱門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