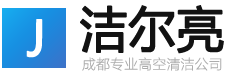“你可以隨時(shí)轉(zhuǎn)身,但不能一直后退”,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句歌詞,出自前不久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民謠歌手鮑勃·迪倫。
以此態(tài)度,來和年輕人蓬勃易碎的玻璃心抗衡,倒是蠻合適。
美國(guó)西部大開發(fā)的時(shí)候,要從西海岸圣地亞哥到東海岸某個(gè)地方,長(zhǎng)3000英里的路程,有兩種走法。第一種走法是:天清氣朗就多走一點(diǎn),刮風(fēng)下雨就先找個(gè)地方躲起來。第二種走法是:不管風(fēng)和日麗還是狂風(fēng)暴雨,每天都必須走20英里。
按照第一種走法,可能永遠(yuǎn)都到不了目的地。
第二種走法,雖然聽起來缺失一種理解性的溫柔,卻能最快速度到達(dá)目的地。
這就是心理學(xué)上著名的“20英里法則”,放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能做到如后者般持續(xù)推動(dòng)自己前行的人屬鳳毛麟角。大多數(shù)時(shí)候,人們都選擇了第一種活法,平坦時(shí)笑意盎然大步流星,曲折時(shí)黯然傷神停滯不動(dòng),天晴我晴,天陰我陰,原本透亮的心,會(huì)逐漸在環(huán)境的影響拉伸下變得模糊不明。
如果你克服不了玻璃心,就永遠(yuǎn)也遇不到金手指。
有時(shí)候,人真的應(yīng)該學(xué)會(huì)自省。王小波說,一個(gè)常常在進(jìn)行著接近自己限度的斗爭(zhēng)的人,總是會(huì)常常失敗的,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內(nèi)的生活的人才總是“勝利”。
優(yōu)秀與平庸之間,往往隔著的不是別人,是自己。
我的一個(gè)讀者阿茶經(jīng)常會(huì)在后臺(tái)留言說,自己在工作上力不從心,辦公室里領(lǐng)導(dǎo)和同事們老是欺負(fù)她,找她的茬兒,感覺像是要孤立她。
秉持著對(duì)事物先了解再判斷的個(gè)人習(xí)慣,我決定耐心聽她把整個(gè)過程的來龍去脈講完,再給出建議。阿茶最近剛換工作,去了一家正處在沖刺B輪融資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做設(shè)計(jì),領(lǐng)導(dǎo)恰恰是她大學(xué)時(shí)期高幾屆的學(xué)長(zhǎng),同樣在視覺傳達(dá)上有所見地。阿茶交上去的設(shè)計(jì)樣稿,經(jīng)常性的會(huì)被他在會(huì)議上單獨(dú)拎出來說,倒也不是批評(píng),只是點(diǎn)名的次數(shù)多了,阿茶心里難免犯嘀咕,這是不是領(lǐng)導(dǎo)故意給自己“穿小鞋”?
時(shí)間久了,阿茶開始覺得學(xué)長(zhǎng)處處都在針對(duì)自己。今天這個(gè)色調(diào)不對(duì),明天那個(gè)調(diào)性不搭,“一張?jiān)O(shè)計(jì)圖,他居然讓我改三遍以上……這不是明顯和我過不去嗎。”
“那學(xué)長(zhǎng)對(duì)于你工作的建議,你覺得還算中肯嗎?”
“平心而論,他對(duì)設(shè)計(jì)方面的很多指點(diǎn)令我傾佩不已,但是,我就是不喜歡他老是反反復(fù)復(fù),讓我去修改一個(gè)不怎么重要的圖紙,太傷我自尊了。”
聽到這里,我大概清晰了很多。
其實(shí)這種事情蠻常見的,五年前,我在給一家風(fēng)頭正熱的青春雜志寫小說,稿子是三審,一切情節(jié)、構(gòu)造、人物、故事背景、環(huán)境描寫,包括細(xì)節(jié)處是否具備邏輯性,都在他們的考量之中。最繁瑣的一次,我一篇稿子連續(xù)改了20多天,每天晚上都能收到編輯反饋回來的不同建議,有時(shí)是角色刻畫力度不夠,有時(shí)是前后銜接上缺乏說服力,就連女主心理自白的尾處是以“句號(hào)”還是“省略號(hào)”作為結(jié)束語,都是我們討論了整夜商討出來的結(jié)果。
人的自我暗示,有時(shí)是很可怕的。
當(dāng)時(shí)我和我的編輯還不算熟悉,曾經(jīng)一度,我認(rèn)為是她在故意刁難我。
出于賭氣的心理,我反復(fù)克制著自己隨時(shí)想要“撂挑子不干”的心理,想要證明給她看,我是有可以寫出好故事的。那篇稿子,刪刪改改,最終放在了比預(yù)期還要晚一期的刊目上。
熱門專題: